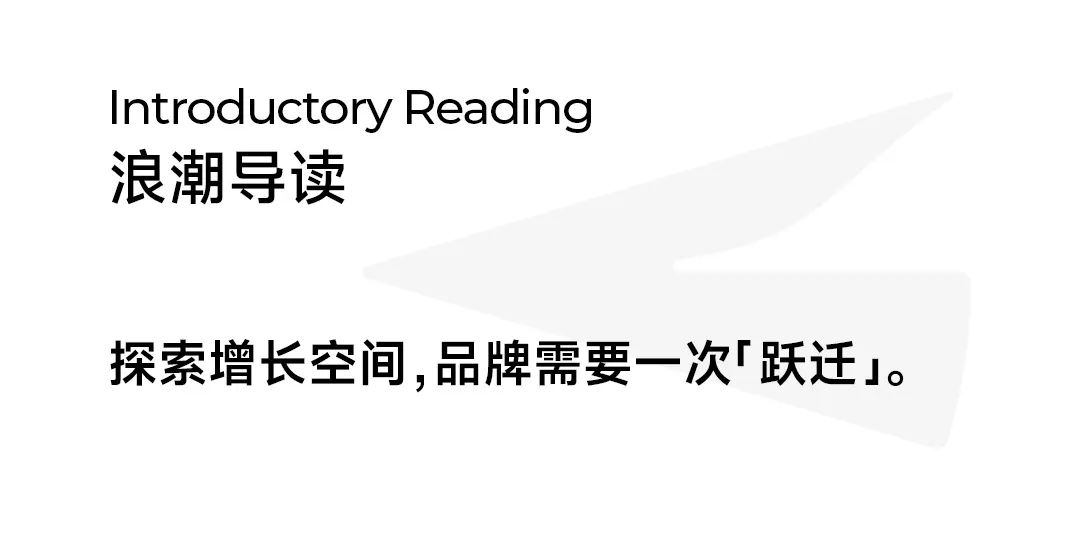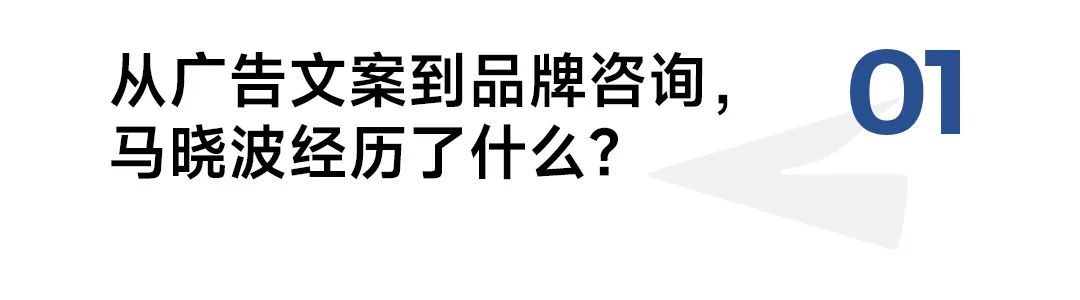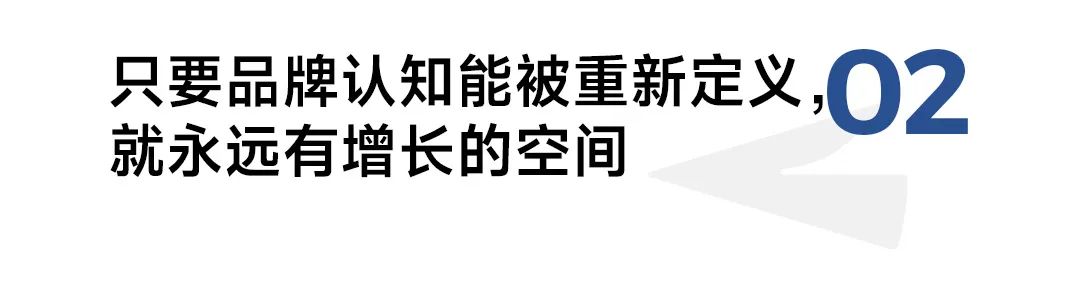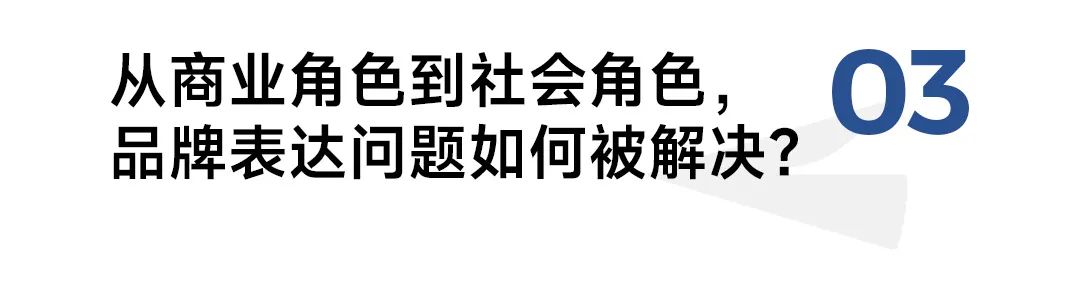这两年,《底线》《上海半分一》《惊蛰令》等品牌广告的出现,让长期深处这个行业的人们都眼前为之一亮,原来商业的东西可以变得这么富有人文气息和情感共鸣。
姑且不论我们可以体会到何种程度,但品牌与公众沟通的探索,让其中许多空间打开成为可能,比如品牌估值得到提升,新的细分市场被打开,良将如潮般涌入。
而伴随着“品牌”占比在消费行业的提升,商业与人文耦合后的能量也有待被进一步释放。
正如这几款品牌广告背后的操盘手马晓波所说,“我们最终还是要用新的概念去引领新的品牌认知,只要认知能被重新定义,品牌就永远有增长的空间。”

这是多少让人有点“惊异”的论断,毕竟市场上涌现出的很多头部品牌,目前也只是裹足于产品或者营销,在公众沟通与价值共识上的探索还在初级阶段。
但相比于一边的无尽内卷,品牌理念的升级和势能的打造,将有可能带来超乎意料的想象。
马晓波更愿意称之为一次公共选举,就是在一个广阔的市场中,你去展示自己认为的未来是什么,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谁会是志同道合的人……形成一个拉选票的过程,最后完成品牌从单一商业角色到独特社会角色的转变。
当然,实践这个转换需要内在的使命且充满挑战,但坚守之后也会迎来真正的品牌复利。而围绕其中品牌存在的盲区、问题,以及过渡的多重路径,最近,浪潮新消费与群玉山咨询董事长&首席策略官马晓波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
深耕咨询、公关及广告行业20多年,马晓波被业内称为「品牌故事大王」,相继服务过方太、中国银联、杜蕾斯、Timberland、快手、bilibili、知乎、蕉内、OPPO、blank me|半分一、ubras、蕉下等国内外品牌,并打造《后浪三部曲》《蕉内三部曲》《蕉下三部曲》等知名作品,其中《后浪》几乎拿下当年所有平台全场大奖。
“他人眼里的波澜不惊,正是我们心中的诗与|风云|。”这是马晓波此前给方太写的一句广告语,就像消费品牌在疫情后的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涌动。群玉山在品牌跃迁上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品牌们正在汇聚的一股强大潜流。
编辑 | 清 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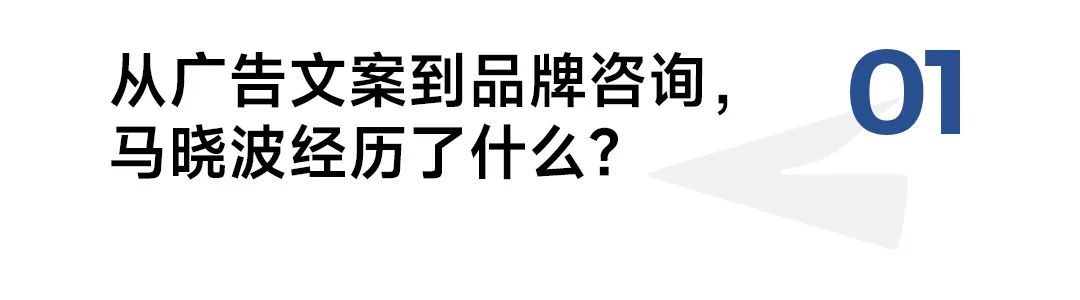
浪潮新消费:你从2002年开始在广告创意行业长期深耕,17、18年迎来了比较强的爆发点,2020年后更是产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
回顾过去这20年,哪些东西在驱动着你不断跨越,经历了哪些关键节点?
广告是一个需要不断寻找意义的行业,它有蛮多让人颓丧的事,但也总会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人,带一些有意思的课题过来。
在我觉得这行比较无趣的时候,这些人带来的新鲜事物,会像突然的相遇一样,让这件事又变得挺有意思的,自己便会从中去寻找或塑造一些意义。
广告文案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职业,一方面人得相信自己写的东西,不然写不好。另一方面,如果写的东西被市场验证过,这又会反过来激励自己。
当你处理完一些课题,反馈不错,自己也很有收获,就有勇气去做下一个更大、更有趣、更具挑战性的课题。
2017年方太刚好20周年,那时候我已经陪他们跑挺久,逐渐磨合到既能释放一些商业意图,又能表达自己想分享的东西。
我们觉得,纪念20周年最好的方式是拍20组家庭的日常生活,于是拍了好多照片。
看着那些照片我也挺感慨,因为过日子跟做事业没什么区别,就是一些柴米油盐,别人看着波澜不惊,但自己肯定经历过一些暗流涌动或者波澜壮阔的时刻。
考虑到方太两款主力产品叫风魔方和云魔方,所以我就写了一句:他人眼里的波澜不惊,正是我们心中的诗与|风云|。这句话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我会不断赋予它一些仪式感或者意义。
浪潮新消费:这几年你们有很多亮点,创业之后,你有没有成为一种社会或者行业角色的期待?
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群玉山摸着石头过河,同行可以摸着群玉山过河,反正不管做成了还是砸了,都算一种可贵的行业经验。
因为群玉山跟传统咨询、广告公司不太一样,有一些课题是结合着战略、战术一起思考,咨询的底子不是特别偏商业,更偏社会学、偏文化一些。
前段时间我们还在想,群玉山到底应该寻找什么样的标杆企业,但国内国外搜罗了一圈,不管是现在的学习对象还是未来想赶超的对象,目前都还没有找到。
浪潮新消费:开启了创始人身份之后,你认为哪些空间被打开和释放了?
马晓波:最主要的还是加深了对职业价值和边界的理解。
我们刚入行所接受的训练都在商业层面,就是通过广告、策略帮助品牌获得更好的增长。价值观边界比较狭窄,你只知道自己在处理的是商业问题。
举个例子,很多全职太太会觉得自己做的就是买菜烧饭的事情。
但当她对自己的认知进一步提升之后,会发现她可以决定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审美取向、价值观念以及幸福指数,她是一个关键角色。像日本、美国,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全职太太越多,生活方式会越先进。
认知打开之后,你会觉得天地非常广阔。所以后来我们慢慢发现,在商业传播里积累到的东西,也可以用到蛮多其他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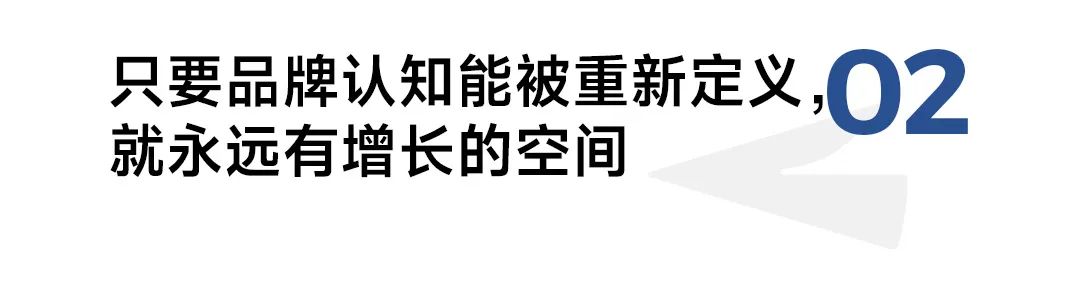
浪潮新消费:在品牌广告行业的多年经营,给你沉淀的最核心能力和价值是什么?伴随着商业、人文环境的演进,它可以改变什么?
马晓波:我们的核心能力既不是创意,也不是研究,而是概念。
它是一切的精神纲领,因为不管是给一个品牌定性,还是给某一种类行为定性,如何准确、感性地去描述,都需要概念来完成。
概念本身代表着,我们对事物性质、发展规律、内外部条件有深度提炼过的认知,同时它还能打破原来的平衡。如果打破不了原来的一些概念,那不管是对事情的判断标准还是话语权,都不在自己手里。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用新的概念去引领品牌的认知,只要认知能被重新定义,就永远有增长的空间。
举个例子,中国广告有两类:商业广告和公益广告。但在这两种之外,还有很多案例无法被准确归类。比如我们做的深圳特区40周年项目。这个项目是为了应对深圳新的发展阶段,重新提炼城市精神,来达成内外部的共识。
这种广告不以商业增长为指标,原来大家会把它纳入到公益广告范畴,但这明显是不对的。
公益广告对旧有共识的不断强化,比如吸烟有害健康、环保对人类很重要、不要乱丢垃圾、要帮助弱势群体等等,而且会指向一种明确的受益者。
但当下这个时代,很多旧共识已经慢慢崩塌,新共识还没有形成,或者说很多领域从未形成过社会共识。
比如怎么看待同性恋群体?宠物是家庭财产还是家庭成员?传统文化应该保护和传承,还是任由它优胜劣汰?遥远的地方发生战争时,我们心里的天平会倾向民族主义,还是命运共同体?
所以前段时间,我们跟几个北大、武大的教授们一起探索这个广告课题,可能会把它定义为“新共识广告”,包含新的价值观共识、生活观念共识等。
新共识广告可以由不同主体来发起,比如政府、社会机构、商业企业,但是最后目的,都是在撕裂、分散的意识里求得一种新的共识。
比如共享出行平台认为,我们应该过一种更加轻资产的生活方式,要摆脱房、车的束缚。但车企就会讲,中国人需要的是私密空间。这背后呈现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完全可以形成很好的社会议题,在争论中沉淀出新的共识。
浪潮新消费:现在我们有很多空间去定义新的概念,因为中间很多东西都变了,但目前并没有被定义清楚。
马晓波:对,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最好玩的一种游戏。因为不管趋势、文化、还是人,都是有办法研究的,但定义概念很依赖想象力和表达能力,一般做策略或者做研究的人,反而做不出来。
前段时间我认识了北大新传副院长刘德寰。他造过两个概念,一个是下沉,一个是“漂一代”,就是在中国城市化进行中,那批漂向大都市的新移民。我很喜欢这个形容,虽然带着一点时代的悲怆感,可是很浪漫。
但放到现在,“漂一代”又可以有新的表达。特别2021年以后,全球大拆解,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进入新的周期,有很多我们原本相信的东西已经土崩瓦解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70、80、90三代都形容为“漂一代”,因为大家就是在时代的洪流里漂流,寻找新的陆地。
浪潮新消费:这种社会概念的重塑如果跟企业、商业结合起来,会有很大的势能。但如果这家企业本身没有那么强烈的驱动和方向感,承载不了这么好的命题呢?
马晓波:战略涉及到未来大的道路选择,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但是在此之前,这家品牌或企业需要在内部取得非常强的共识,他们要发自内心地认同这件事情。
所以像概念也不是单纯由我们创造的,它是和品牌共创出来的。
我们也发生过好几次,到后面无法跟客户在核心价值观层面取得共识,你不可能逼他做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所以这种合作就会终止。
浪潮新消费:这个时代,头部或者优质品牌跟消费者、跟社会沟通,存在的盲区或者沟壑在哪里?
为什么现在ESG概念比CSR更先进?因为它是鼓励企业把社会责任跟主营业务捆绑,否则有钱的时候多做,没钱的时候少做甚至停掉,就没那么可持续。
其实品牌最需要思考的是,自己在社会里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为了解决什么大的社会问题而存在。
很多时候大家太关注短期实利性,缺乏一些更加务虚的思考。但中国企业放到全球看还太年轻,还没有真正跨越过周期,所以对于社会角色和社会价值的认知还不太够。
而且这跟中国的发展状况有关系。前40年,本土品牌就需要拼命地增长,要生存下去。大家可以去做慈善、公益,但不断增长就是那个阶段的使命。还没超过30亿营收的品牌,最主要的社会责任就是产品责任。
但是继续往下走,国内现在头部的这批企业,如果对应中国当下的发展目标,首先自己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其次能够内生外化,把一部分能量赋能到其他行业。
中国制造业本来是为全球准备的,现在一脱钩、一拆解,大量的产能无法释放,质量又良莠不齐,非常需要把多余、低劣的产能挤压出去。
所以能帮助中国做产业升级,助力实体经济,就是承担社会责任最好的方式。现在阿里、腾讯都在讲这个事情。
以前说跟做是两套东西,现在不管基于哪种原因,大家重新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价值之后,起码应该比2020、2021年更清晰一点。
浪潮新消费:这几年疫情或者环境变化确实是一个转折点,让人意识到应该做更高价值的事情,而不是做无止境的增长。但他们在品牌表达上还缺些什么?
马晓波:表达是执行层面的东西,它并不需要太复杂的技巧。就像写文案,如果企业的思考明确和准确了,表达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绝大部分企业的问题是言行不一,内部缺乏必要的共识,导致行动混乱且分裂。
浪潮新消费:所以群玉山还是要帮助那些认知相对清晰的品牌,去解决更深刻的问题。
但类似于这些优秀品牌的认知也很高了,有自己的方向和目标感,那你们具体是如何识别其中的矛盾,去真正地找到一个适合的路径帮助他们?解决方案是怎样形成的?
马晓波:最早的时候,我们也按照行业跟赛道分出汽车组、快消组、美妆组等,因为那时候觉得,在一个行业里深耕,效率会更高。
但2019年开始,我们就不大采取这种方式了,一方面是广告行业人力大量流失,无法再组织起非常规模化的人力。
另一方面,深耕某个行业有时候会做得很深入,但它不利于以更广阔的视野去对比不同行业、赛道、阶段的品牌,总结出一些真正具有普适性的经验和方法论。
后来我们以课题做区分,比如“一个品牌如何实现从小众化到大众化?”或者“淘品牌怎么成为一个公共品牌?”。这样的话,不管是牛奶、鞋类还是童装品类,都能找到相似的路径以及资源配置方式。
再到后面,我们探索的“品牌公共角色”慢慢成型,但后来又发现,它只适合服务行业头部或者比较成熟的企业,比如厨电领域里的方太、短视频领域的快手。
因为这些企业需要经历再一次的跨越,从商业企业转换到社会企业,需要更加系统地梳理品牌资产和社会功能。不到100亿的品牌,可能还需要你帮忙积累资产,而不是梳理资产。
所以后面我们有条横轴,从品牌商业机构慢慢过渡到社会功能组织,按照这条路径,可以分为4个类型:定位、赛道跃迁、品牌价值壁垒和品牌公众角色,去对应不同发展阶段品牌的问题。
比如蕉下、蕉内这批从10到50亿左右的品牌,赛道跃迁最适合,因为他们还面临着如何构建更大的增长空间,去解决三到五年内快速增长的问题。
我很喜欢一幅画叫《拾穗者》,就是农民在麦田里弯腰,捡拾稻穗。这跟现在企业的处境极其相似,麦田已经被收割空了,大的集中性消费也结束了,后面无非就是捡拾一些零散的需求。
以往《定位》思想,其实容易把品牌的空间越做越小,因为它寻求的是如何在细分赛道里做到第一。
在行业总量快速增加的时候,比如前几年地产业经历过好几个高峰期,所有跟它关联的大家居、小家居都在增长,那时候去切分细分赛道没有问题。
但如果行业进入平缓期或者下行期,你还坚守着细分赛道,基本上活不好。不管在存量市场里怎么卷,可能从高维跨过来一个对手,就能把你们全拍死。
赛道跃迁是趋势化的研究。比如蕉下物理防晒的增长空间已经到上限了,各种快时尚品牌、传统户外品牌都往这里渗透挤压。
但如果它通过户外场景解决方案,加户外生活百货、户外社群服务,组成一个更大的轻量化户外的赛道,从个人决策上升到家庭决策,就有了非常大的增长空间,意味着可以同时服务中国近4亿中产人群。
举个例子,轻量化户外不是探索型、硬核型的,而是享乐型的户外生活,所以一切能让人感到开心,能增加人与人亲密度的户外产品,都可以做。
酒也可以,像清酒或者低度酒通常在shopping mall的B1楼,但那里也可以有户外类型的酒,只是在设计上需要把包装做得更轻量、更易分享。
当然,鞋、冲锋衣、帐篷这些东西肯定得有,但服装一般在3-4楼,专业装备可能要跑到6-7楼。赛道升级、赛道跃迁就是把不同货架全部打通,但赋予它一个新的概念,构成了户外生活的整体解决方案。
文章来源:【浪潮新消费】公众号
【声明】该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大数跨境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代表大数跨境观点或立场。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如发现本站文章存在版权问题,请联系:
contact@10100.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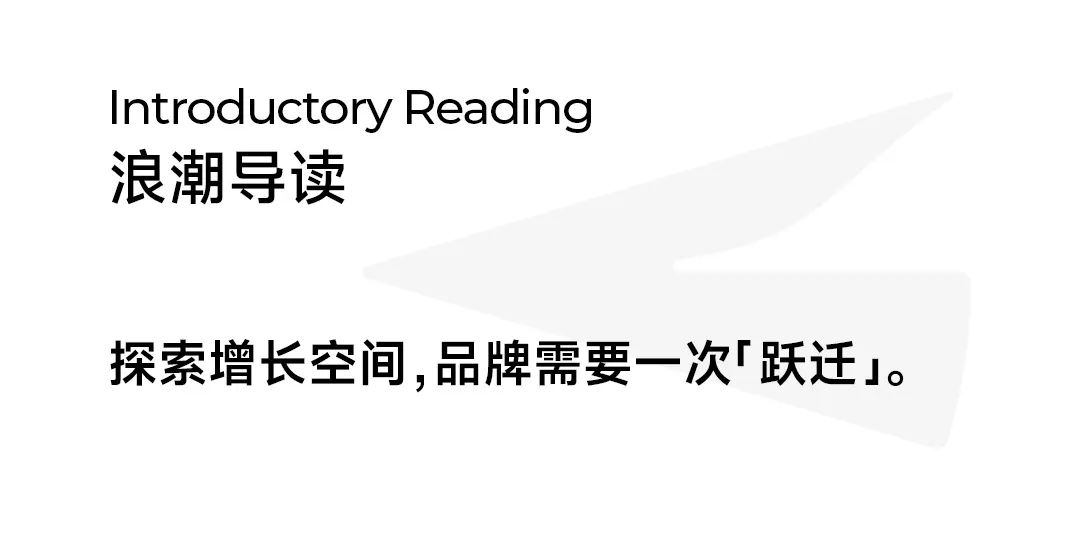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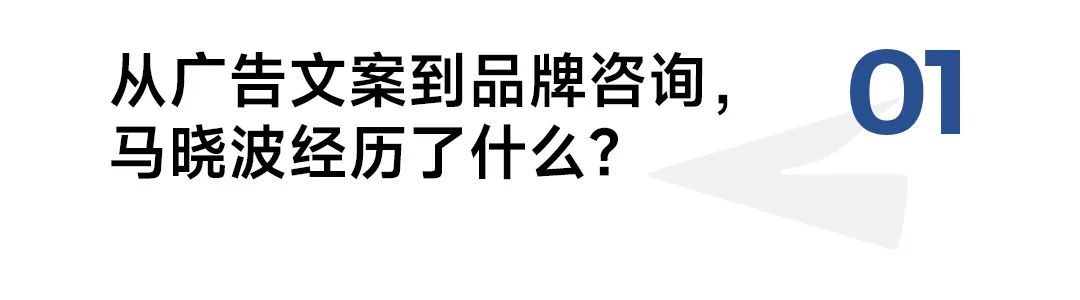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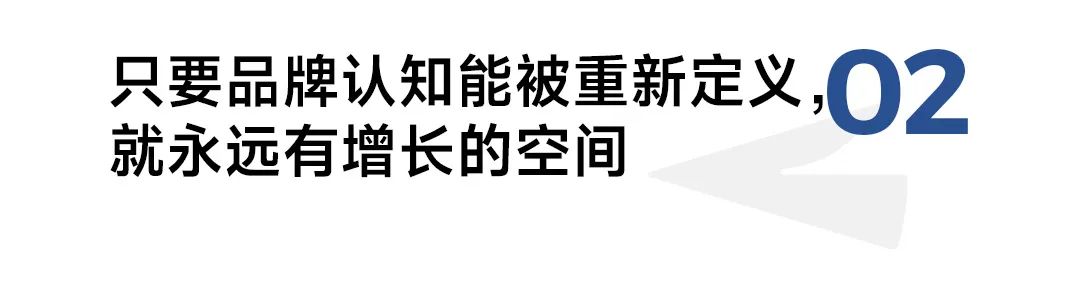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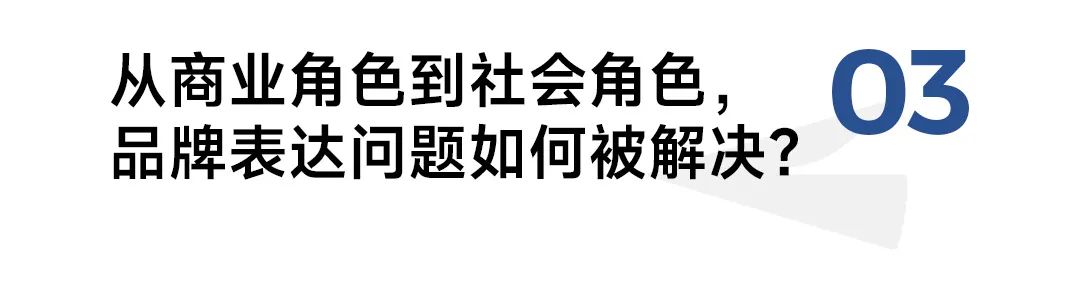

 浪潮新消费
浪潮新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