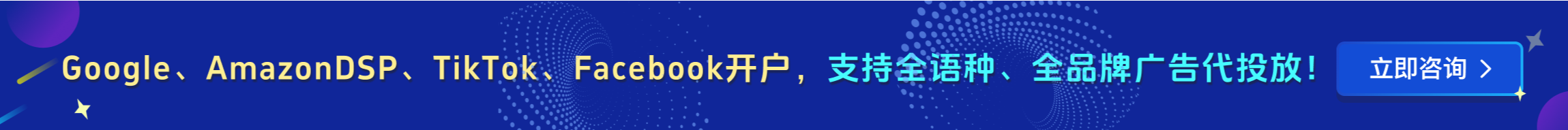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中高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阶段,实施金融安全战略是保障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金融危机使高收入国家跌回中等行列
多国的发展经验表明,金融危机会对国民经济产生全面、长期的负面影响。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使巴西、智利等国的人均GDP出现了10%以上的下降,并且直到1987年前后才恢复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见图1);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使东南亚国家的人均GDP出现了近10%的下滑,直到2002年前后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见图2)。
如果金融危机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激化其他社会矛盾与风险将会造成更长期的经济衰退。例如,阿根廷的人均GDP直到1994年才重新回到1980年的水平,而印度尼西亚的人均GDP在2005年才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
综合大量学者的测算,中国有望在2025年前后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里程碑。然而,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稳定地跨越到高收入国家门槛并非易事,有许多国家在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经历了大的经济波动,重新“跌落”回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见表1),其中,金融危机是出现这类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
图1 阿根廷、智利与巴西三国人均GDP指数

注:按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以1980年为基准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作者计算
图2 泰国、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人均GDP指数

注:按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以1997年为基准年。
表1 跨越高收入门槛经济体发生“跌落”的典型案例

注:阿根廷曾于2014年被世界银行归入高收入国家,但其有关经济数据发生了重大修正。由于世界银行并不依据国别数据修正调整以往的经济体分类,相关分类没有被更改。
与金融危机有关的“跌落”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经济体自身金融不稳定引发的危机。例如,韩国在1995年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但随后到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使其跌落回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直到2001年才再次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阿根廷在21世纪头10年经历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于2017年跨越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门槛,但随即于2018年发生货币危机,进而导致严重的货币贬值与资本外流,引发经济衰退,跌落回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至今没有再次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
第二类是外部金融冲击导致国内金融风险集中暴露,引发系统性动荡。例如,拉脱维亚在2000—2007年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在2009年跨越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门槛,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外资撤退使被高增长掩盖的经济过热、高通胀、债务积累等问题集中暴露,引发该国严重的经济衰退,于2010年跌落回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12年再次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类似地,匈牙利也在21世纪初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并于2007年进入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其高度依赖外需与外部资金的风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的冲击下集中暴露,经济增长率从2001—2006年的4.3%下滑至2007—2012年的-0.6%,于2012年跌落回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14年再次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
第三类是国际制裁导致的金融动荡。在大宗商品价格与国内经济改革等因素的推动下,俄罗斯经济在2010年前后经历了较高增长,于2012年跨越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然而,2014—2015年欧盟、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因国际政治冲突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制裁,打击了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进而引发卢布贬值、资本外流与经济衰退,使其于2015年跌落回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金融安全“新”形势
近年来,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金融安全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第一,防范金融风险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地方政府举债更加规范,影子银行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委托贷款与信托贷款存量从2017年底的22.5万亿元下降至2020年底的17.4万亿元,占社会融资存量的比例从10.9%下降至6.1%。房地产行业的信贷占用稳步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加大,2017—2020年的处置金额为8.8万亿元,超过此前12年的总和。实际运营的P2P(点对点网络借款)机构已经清零,互联网金融发展进一步规范化。
然而,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依然繁重,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仍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中国经济宏观杠杆率在2017—2019年由快速增长转入稳定,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宏观杠杆率在2020年再次上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测算,2020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提高了约26个百分点,其中非金融企业提高了13个百分点,家庭部门提高了5.6个百分点,广义政府部门提高了7.7个百分点(见图3)。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回归常态,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的同时也应防止新一轮金融风险积聚。因此,应对国内金融风险积聚仍是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挑战。
图3 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

注:Q表示季度。
第二,国际金融环境更加复杂。近年来,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当局通过量化宽松等工具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在这一背景下,当前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首先,国际主要无风险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主要经济体无风险利率进一步下跌,截至2021年3月伦敦同业拆借利率(6个月,美元)降至0.2%,是1963年以来的最低值。其次,各国债务激增。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测算,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达277.7%,其中发达经济体为310.6%,新兴市场经济体为225.3%,均为过去20年的最高值(见图4)。最后,发达国家政策与风险的外溢性增强。随着全球经济、金融联系日趋紧密,并且“低利率、高债务”使投资者对金融脆弱性的担忧进一步加深,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给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收支、汇率稳定都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当发达国家进行量化宽松操作时,国际资金往往快速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以赚取收益,带来本币升值、热钱流入的压力;而当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收紧时,国际资金则快速回流以规避风险,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贬值与资本外流的压力。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第三,金融制裁与长臂管辖风险突出。美国的金融制裁可以分为针对个人与私人部门银行的单点制裁、对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制裁、对中央银行的制裁以及对特定国家的紧急资产冻结四类,并可通过次级制裁手段对所有与被制裁机构和个人进行交易的第三国实体进行惩罚,从而达到将被制裁的个人、机构、国家封锁在美元金融体系之外的目的(郑联盛,2020),在中美博弈中,必须坚决维护中国金融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工作准备,及时阻断风险。
第四,数字金融的有效监管模式仍有待探索。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发展的新亮点,相关技术也在金融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为提高融资效率、增强金融普惠性做出了贡献。同时,金融科技的发展也给维护金融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比特币大幅波动可能引发资产泡沫,其匿名性则为反洗钱等违法行为提供了便利;一些金融科技企业通过向其他传统金融机构提供大数据信贷风险评估服务参与贷款业务,可能产生监管套利,带来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各国针对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治理缺乏有效合作框架,诸如数据跨境流动、央行数字货币联通交互、数据资产产权归属、用户隐私保护等问题都需要增强国际共识与协调机制。
实施金融安全“新”战略
在上述国内、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大背景下,实施金融安全战略、有效维护金融安全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进一步巩固防范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成果,防止“黑天鹅”与“灰犀牛”引发金融动荡。一方面,应继续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优化债务结构,稳妥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资金等风险。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增强逆周期调节能力,搞好跨周期调节,防范输入型风险,降低其他国家的政策调整对国内金融环境的负面影响。
第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建设,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互利合作关系,提升贸易、投资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比重。对标高水平多边贸易投资协定,实施高标准的金融双向开放,推动金融市场会计、评估等基础性制度改革,逐步改变资本市场管道式、分布式开放模式,推进制度型开放,提高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牢牢掌握人民币利率、汇率定价权,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审慎监管,健全金融市场外资进出的监测与预警机制。
第三,审慎监管金融科技。坚持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宗旨,增强金融普惠性。坚持金融持牌经营,所有金融业务活动都要纳入监管。坚持风险为本、技术中性,把技术风险监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增强监管的协同性、有效性,切实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坚持金融科技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推进中国版“监管沙盒”机制建设,处理好创新和规范的关系。